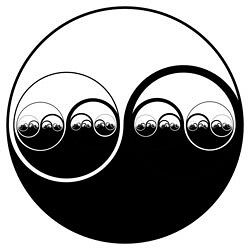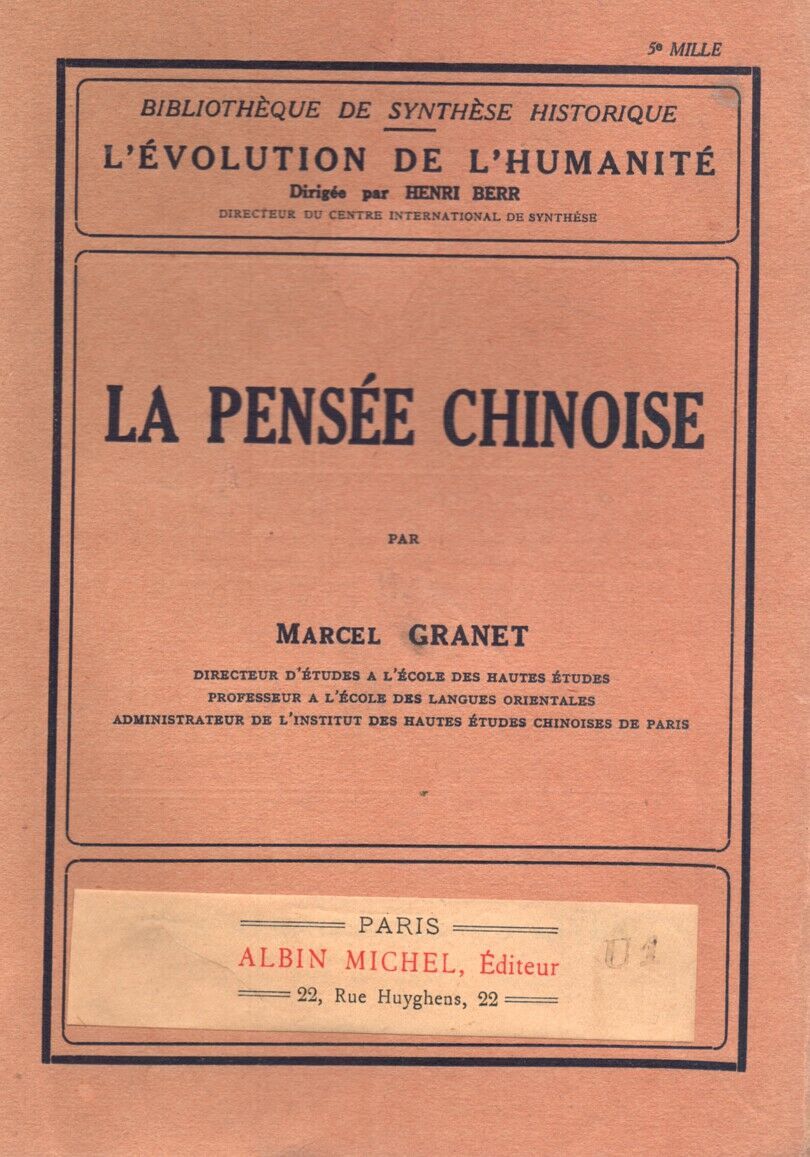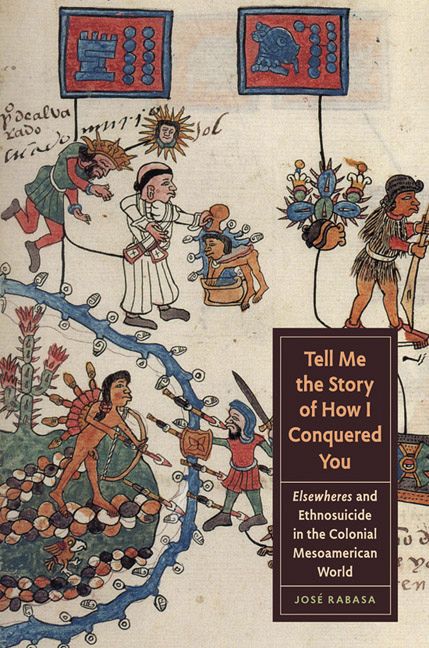编者按:
《黑齿》杂志的“将来完成式|2021年终问卷”系列尝试从过去的文章中找到对当下仍旧有效的提问与答案。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来自2018年的卦辞:“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在对这句卦辞的运用中,理论家向在荣将易经放到跨文化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尝试借由对易经的理解历史,来拆解当代的二元论意识形态。本文原以讲座形式发表于2018年柏林世界文化宫展览“新石器时代童年——1930,错误年代的艺术创作”(Neolithic Childhood. Art in a False Present, c. 1930)其系列论坛“1930,深层时间和危机”论坛(Deep Time and Crisis, c. 1930)。
在一篇2012年的e-flux journal中,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论述拉康派精神分析是如何处理一与二的数学关系,开篇即是他称做“60年代毛派口号”的文章标题——“一分为二”。他感叹道,这个口号在今天不只是显得过时,当今的学生根本不可能理解:“没有人会知道是谁说过这句话,或者知道它有任何意义,就像是在说中文一样。”1Mladen Dolar, “One Divides into Two,” e-flux Journal #33, March 2012. https://www.e-flux.com/journal/33/68295/one-divides-into-two/.作为说中文的人,我当下白眼翻了不只一次,而是两次。这都2012年了,怎么还有人整这种无聊的笑话? 早期共产党内部的一场著名的论战,通过“中文莫名其妙”(inscrutable Chinese)这个古旧的殖民转义,企图为多拉尔发言增添幽默色彩。尽管人文学科中,不断重复地对东方主义批判已经扁平到近乎教条化的地步,但现在看来,重溯其批判原委还是有其政治必要。
在此之前,让我先分析一下自己的反应:为什么这则笑话特别令人震惊?一方面,因为笑话居然在2012年还被用来比喻毛派口号之于他的年轻学生是过时和陌生的。即便中文涵盖了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使用人口,还不算上多少人在研究这门语言,仍被作者认为是莫名其妙,只为了衬托出“一分为二”这个口号在时间上的落后,和空间上的怪异,好让作者提出他的拉康式政治哲学方案为其续命。
我自问,如果这是一篇1932年写的文章,我还会有同样的反应吗?我看1932年的傅满洲电影,读1965年的《傅满洲的脸》时,可能不会对此走心,这件2012年的事看似无伤大雅,但确实让人感到不是很舒服。在这背后,我对2012年和1932年的双重标准也许另有深意。我似乎认为,种族主义等种种结构性的偏见应终有一个到期年限。我原以为,当中国如今已不再扮演欧洲殖民主义受害者,而跻身全球列强之列,有这么多对此强权的报道,分析和批评,中文莫名其妙之说应该早已走入历史。我承认,这种相信“情况会更好”的想法,是掉进了线性历史发展论的目的论陷阱。
在现实中,我们被卷入一系列危机风暴,近年来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强势回归,搭上了特朗普当选,以色列近期于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的屠杀,甚至是极右派的德意志选择党(AfD)进入德国议会,寥寥几个极端的例子和我当初对一本极具批判精神的期刊刊载种族主义笑话的惊吓似曾相似。当“欧洲中心”仍持续被各种莫名其妙的“它者”所袭扰,让我们暂用“莫名其妙的中文”来充当各种“他者”——原始人,野蛮人,难民,不一而足——的代名词,它没有过期时效。它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结构性节点,也是关于思想史的历史叙述中被反复叙述的版本。若要破除这样的叙述,那就要进入其中二元论思想的核心进行内爆。
走进展览“新石器时代童年——1930年代的错误年代艺术创作”,眼前出现各种“他者”群体,巴比伦,纳瓦特,中国,以某种错时和神秘的方式被放到一起。展览围绕着德国作家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的“艺术考古学手册”为中心,探索1930年代的欧洲如何观察古代艺术,文学和哲学文本,又如何将它们视为理论资源,来重新思考诸如性/别、宇宙观的交错纠缠、以至于政治解放等种种当代议题。展览尝试消除欧洲前卫艺术纯粹性的想象,以及对历史的线性叙述预设,也尝试警告我们那些长达一世纪后仍旧盛行的偏见,作为回应,我的阴阳跨二元论会从易经被介绍到欧洲的1930年代思想史历程开始讲起。
关于中国哲学的两部重要著作于欧陆的传播,正是出现在与傅满洲共时的1930年代:德国传教士及汉学家尉礼贤(Richard Wilhelm)在中国硕儒劳乃宣的指导下,于1924年出版了德文的易经译本(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而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也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关于这些书籍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童年期”,这个问题就留给其他历史学家来回答。本文首先将介绍什么是阴阳跨二元论,其次,我将具体说明,如何以阴阳跨二元论来解构与批判当代话语中,特别是围绕“后殖民整体”的辩论中,如何总是潜藏着一种 “非a即b”的替代逻辑。而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将简短地回望30年代,以重新审视当时的思想传播状况,其百花齐放,有一段非常去中心化的全球流通、渗透的情景。
一、阴和阳
什么是阴阳?人们常讲说是男女,或者各种其它二元对立项,这就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精神分析研讨班说的:“阴与阳,众所皆知,是关于男与女的概念。”2Jacques Lacan,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2001: p11-22.认为中文莫名其妙的姆拉登·多拉尔也在同一篇文章中详尽解释阴阳的概念,代表了“阴性和阳性的二极(并且只能是二)”。他也引用了所谓的“道家阴阳符”并认为这是“有力的论断”,接着写道:“它说明的是关系。并且是性关系。而所有关系都不脱性别。”3Mladen Dolar, “One Divides into Two,” e-flux Journal#33, March 2012. https://www.e-flux.com/journal/33/68295/one-divides-into-two/.如果你熟悉精神分析,这句话听起来肯定不陌生,让我们想起拉康的名言“不存在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确实,这段关于阴阳的解读,算是拉康论性别差异的少数反例(这并非本文讨论的方向)。姆拉登·多拉尔如此自信地对 “道家阴阳符号”夸夸其谈,但他的文章参考完全就只写了拉康的研讨班,仅仅用一个二手解读,就足以让他声称“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对物质(hyle)和形式(morphe),阴性和阳性的定性,就是我们的西方版的阴阳学说。”4Ibid.中国长期的男权统治历史,以及普遍存在的异性恋本位思想,确实有助于确证这种将阴阳简化为二元性别等级阶序的论调,即便这样,我还是不免想到,在2012年,阴阳的概念遭遇了粗暴的殖民。阴阳被缩减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概念。在此仅简要列举几个阴阳学说的戏剧性转折:史前神话起源:“女娲为阴,伏羲为阳”,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对《易经》的运用,在公元前5至 2世纪,战国的儒道思想对周易的再诠释,特别是公元前1至2世纪以汉儒董仲舒为首的在儒家宇宙观中对阴阳的层级化,道德化,同时也是异性恋本位的阐释。直到11至12世纪,宋代以周敦颐和朱熹为首的新儒家对阴阳学说的复兴。这一切复杂的变化在姆拉登·多拉尔的文章里被粗暴简单的概括,而用以遮蔽阴阳漫长三千年历史的,竟是一个来自New Age心灵文化的推广网站“OneiromancerNJV”拿来的所谓的“阴阳插图”?
在此,我想将注意力聚焦在阴阳概念形成的时间段,特别是在它在汉代被固化的时刻之前的阶段。当我们说阴阳,我们总是先说阴再说阳。这也许已经暗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至少与男女出现顺序是相反的。在汉语里,我们从来不会颠倒过来说:“阳-阴”。拗口的发音提醒我们应该停顿片刻,让我们不会太快将阴阳归结为一种跨文化、普世皆准、跨越历史藩篱的父权制神话的象征物。
从词源上看,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告诉我们:“阴: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 5许慎,《说文解字》1923年夏,尉礼贤(Richard Wilhelm)则在北京用德文进一步对此提出注释:阴是指“阴天”,“阴影”;阳是指“阳光下的”亦即“高,明亮”的事物。换言之,阴阳非关性别。即使在公元前2世纪,汉儒董仲舒开始以阶位秩序进一步为阴阳提出划分时,性别差异也仅仅只是无数种阴阳表征的其中一种相对重要的形态而已,却并不是一种本质。在阿伦卡·祖潘切奇(Alenka Zupančič)的“性别差异及本体论”一文中,阴阳更与其他“传统本体论及传统宇宙观”混为一谈,作者并声称,它们的运作“有赖于对立项(通常是性别化的)的存在”。 6Alenka Zupančič, “Sexual Difference and Ontology”, e-flux journal #32, February 2012. https://www.e-flux.com/journal/32/68246/sexual-difference-and-ontology/斯拉沃·齐泽克(Slavoj Žižek)也多次在证明黑格尔辩证法的独特性时,每每将阴阳贬抑为前现代包山包海的观念,用他的原话,阴阳“是关于两种对立的力量和法则,两者守衡。”7Slavoj Žiž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Verso, 2007, pp. xxvi.这些都只是学术上的例子,但你完全可以看到,将阴阳视为性别差异,或更直白地将其视为“与东方智慧的水乳交融”的例子简直是无所不在,从性爱手册到按摩精油或身心平衡的草本茶饮,来到你的面前。
当然,这些将阴阳简单化约为另类传统,“原始”二元论的生活风格实践并不出于汉学家之手笔。也没有人会要所有人都去读道德经或易经,遑论他们也不会真的去读。不过,如果要谈谈这个中国哲学最精深的思想——甚至对它提出批评,那看不懂中文,至少应该从欧洲丰富的汉学传统中寻找一些资源,无论这个学科的构成有多么“东方主义”。尉礼贤于1923年写下影响广泛的《易经》德文版〈导论〉便十分适合用来对以上列举的简化论调进行批判:
然而,诺斯底式的二元论猜测与推论和原本《易经》的概念无关……当时《易经》往往被当作一本巫术书使用,在过程中大量各式各样原本不在其中的事物被解读出来。自然地,以阴阳、男女作为原始法则的学说,也引起了研究中国的国外学术界的关注。顺藤摸瓜甚至出现了以为阴阳是一种阳物崇拜的原始符号的说法。不过,可能让他们颇为失望了,阴阳二词在愿意上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证明他们的“发现”。 8Richard Wilhelm, Introduction,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Cary F. Bayne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1968.
同样,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在他的重要著作《中国思想》也发展了他对阴阳的详尽阐述。而他也反对:“借用西方哲学家现成的语言来阐释这些中国符号[…]从他们的定义发展论点,并将中国思想阐释成一种本质主义的二元论。”更具体地说,他在1934年,早已向后来齐泽克这样的哲学家提出批评,道:“阴与阳并非本质,非力量,非法则”。9Marcel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Paris: Renaissance du livre Albin Michel, 1934, pp. 101-9.
实际上,这牵涉两种相反的趋势持续地相互转化(如,白天和黑夜,向光与背光)。并没有任何清晰的分界可以划定其相互流动的途径。它们并非可以被“合二为一” 的两种相互分离的实体或力量。儒家《易经系辞》道:“一阴一阳之谓道” 10[魏王弼,《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北京:中华书局,2011,345。];道家《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为了弄清复杂的阴阳关系,并避免将阴阳误以为是一种性别差异的存有本质,或任何其它事物的存有本质,我想强调阴和阳的“相生相克”,这在现代语言学中并不这么容易理解:阴与阳的相克意味一种非a即b的“either/or”,但同时,它们的相生意味着既a且b的“and”。正如道德经开篇所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11老子,《道德经》重要的是,这两个“过程”根据四季节气发展出事物变化的四阶段,《黄帝内经》再细分出另外两阶段,总共是: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等六个不同程度的状态,这也在张仲景《伤寒论》中得到完整的阐述。
二、“非此即彼,亦相互生成”的跨二元论
关于二元论思维,非此即彼的“either / or”是这种思维的空间表述,而“之前/之后”则可以说是其时间性的表达,以至于一系列“转向”的生产都是如此:语言学转向,视觉转向,情感转向,生态转向,本体论转向,去殖民转向。跨二元论(transdualism)尝试在批评二元论的同时不重蹈二元论的“非此即彼”模型,这个模型常常假装超克或推翻二元论,却仍旧被锁定在一个欧美中心的线性谱系之中。反之,我对跨二元论作为批评空间的使用,则是要向下潜入分裂主义“非此即彼”( either/or)的逻辑之下,将它篡改成“非此…也是”(either …and)的逻辑。其中,“非此”标志着事物的独特性,标志其“身份”、特质和趋势;而 “也是”则标志着他们的依存和纠缠,以及它们相互碰撞并成为对方的倾向,并使独特的“身份”显得转瞬即逝。
葛兰言的法译版本将儒家的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解为:“一个阴时,一个阳时/一个阴面,一个阳面,之谓道”。这版翻译注意到了阴与阳在时空中相互纠缠的特质,葛兰言以此强调阴阳并非某些具体力量或法则,而是一些面向(aspects),或他所说的“象” (emblems)。他也正确指出,若要理解这些时空纠缠,就必须知道:“道字隐含了易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他将易译为“变异”、变译为“循环”,通译为“相互穿透”。12Marcel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Paris: Renaissance du livre Albin Michel, 1934, pp. 105.简言之,《易经》的阴阳研究异与同的相互变化,道探讨变与不变。《易经》的标题我们原该如此看待:关于变异(易)的不变之道(经)。“跨二元论”中的“跨”正是遵循“易”的多重含义,暗含轻易(弗兰索瓦·于连说的“默化”),可变性和不变性。
除此之外,阴阳跨二元论更重要的概念是葛兰言翻译为“相互穿透”(interpenetration mutuelle)的“通”。13Ibid. “通”既被动也主动,它意味着穿刺、弥漫。 实际上,它是事物的理想状态。俗话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我想举一个我并没那么钟意进入的论战为例。欧洲“拒绝承认他者的渗透”确实特别能说明我谈到的阻塞、上下不通,由此,跨二元论的主客方程式才能告诉我们历史的形态,以至于未来的形状。
在2018年,伊兰·卡普尔(Ilan Kapoor)为齐泽克(Slavoj Žižek)充满问题的“批判性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辩驳,他说,去殖民理论家如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和哈米德·达巴希(Hamid Dabashi)等人对齐泽克的批评不过就是:“将非欧洲的特殊性错当成一种本真性,仿佛在殖民主义和资本全球化之后还可以回到一种原始独特的非欧洲身份。”这种论调听起来不是很熟悉吗?确实,在他们看来所有事情都可以归结到欧洲现代性的天罗地网。这还没完,作者的欧洲中心总体化理论还在不断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再下一页,作者声称:
齐泽克无非是暗示,经历欧洲帝国统治后,欧洲的象征秩序便是当前事实上的全球象征秩序,因此,全球南北方的后殖民主体除了与之合作外,别无选择。14Ilan Kapoor, “Žižek, Antagonism and Politics Now: Three Recent Controvers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Zizek Studies: Vol. 12, No. 1. 2018, pp.7
对于任何曾与欧洲以外的文化——或者说欧洲的现代性以外的文化——真正打过交道的人们,恐怕都会直接无视这种过度自信的论点。提出“激进的他方”(radical elsewhere)的学者何塞·拉巴萨(José Rabasa)研究墨西哥本地阿兹特克的纳瓦文化在西班牙占领后的幸存生机,特别是运用拉丁语、西班牙语和那瓦特语三语工作绘制图典的阿兹特克画工抄写员(tlacuilos)。他都不屑将以下的观点写在正文,而是在脚注中写道:
“我们在[特莱利亚诺-雷曼西斯手抄本]第46r页中凭直觉感受到的“他方”恰恰打破西方入侵带来单一历史、单一世界叙述这样的证词。”15José Rabasa, Tell Me the Story of How I Conquered You: Elsewheres and Ethnosuicide in the Colonial Mesoamerican Wor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2011, pp 107.
确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直接研究他者,但,认真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则不是什么非分的要求,特别对任何负责任的学者来说。而面对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搬出法农(Franz Fanon)批评欧洲象征秩序别无选择的说法,这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也以法农回击:“法农和黑格尔、精神分析、萨特甚至是拉康的接触不可不谓深入”16Slavoj Žižek, “The Impasses of Today’s Radical Politics,” in Crisis & Critique #1, 2014, pp. 6。因此,正如齐泽克本人和这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的捍卫者一样,法农很可能也是“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只是,这个说法要成立,除非我们否认海地革命对黑格尔的影响(Susan Buck-Morss),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对萨特的影响,而爱德华·萨义德也曾经告诉我们作为“非欧洲人”的摩西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至于道家和儒家的影响,拉康也在第十八场研讨会上直接借鉴了中国哲学,并承认:“要不是我以前学过中文,我不可能成为拉康派。”
伊兰·卡普尔的论点是:“西方遗产[...]当然可能是(也确实是)帝国统治和掠夺[...],但也提供了它自身(及其批评者)衡量其过去的准绳”,这也呼应了一些急于否认任何去殖民的尝试都是“本土主义”和“对想象中的过去的一种怀旧”的批评话语。欧洲中心主义,包括“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内,完全是拒绝承认他者渗透的重灾区。对他者渗透的否认 (denial of pervasion),以及对与研究主体共时性的否认(denial of coevalness;Johannes Fabian语),正是欧洲中心对他们认为的“欧洲遗产”之反应,也是对“莫名其妙中文”的反应。如果我们必须接受后殖民是普遍和总体状况,也即是说一种相互渗透的状况——尽管是不受欢迎的一种渗透,曰殖民主义强加于人,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揭穿如下思想:即,欧洲自我发明,自我创造,无中生有(ex nihilo);欧洲的思想家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拉康等人也奇迹般地,仿佛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解放性的理论。
三、1930年代的乱国际主义:差异的纠缠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通”的概念,卡尔·爱因斯坦的主/客方程式正是这样告诉我们:事物相互可穿透。我结合两者,称之为“跨二元论的主/客方程式”。首先,当“穿透”这个词太过暴力,太过阳具钦羡,太过于殖民气,作为互补,在此,也许“通”可以转而聚焦在一种遍在的状态。跨二元论的主/客方程式并不放弃主体、客体、或者阴阳二元。换句话说,差异本身并不是问题。不仅如此,我们有赖差异来实现“跨”的动作(transing)和多孔渗透的可能。
跨二元论的主/客方程式意味着:阴阳的差异相互缠绕,其同中有异。它主张二元论对人们自身内在去制造世界,认识世界而言是有效的,同时,它也突出了阴阳的酷异性,以这种变异的特质,阴和阳既能相互辨别,又彼此相通。
在展览中,当时的欧洲艺术家及知识分子“正在寻找新的头绪,他们对所有古老文化,对‘深度时间’,对人类‘童年’的重新探索,正在酝酿一种新的批判意识“,而这时候的上海等其他全球性城市,他们则不得不寻找自己的现代性道路,以应对年轻共和国的深度危机。鲁迅,丁玲,萧红和郁达夫的左联当时则在着手重新发明中国文学作品,倡导世界主义,女权主义和全新的性别意识。同时,孟加拉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影响了新月诗社,诗人徐志摩,胡适和沈从文等成员组成了新文化运动。施蛰存创立了《现代》艺文杂志,制定明确的编辑政策,以使其与任何单一的政治或艺术运动保持距离。
去年在北京泰康空间举行的“重探中国现代主义”研究项目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艺术评论家董冰峰将30年代,特别是《现代》杂志定为中国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并反对将中国现代主义的兴起统一看作是翻译,殖民历史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认为现代主义只从西方发源,再随后影响其它地区的狭隘观点,就举爱森斯坦的例子吧。我们甚至不需要强调爱森斯坦受过多少墨西哥的文化影响,如果打开这个墨西哥的潘多拉盒子,那会需要另一篇期刊专题论证种种思想交流以及文化影响。我只想简单提一下他的电影制作中鲜为人知的方面:他汲取中国戏曲和日本歌舞伎,特别是京剧diva梅兰芳,回头研究中国古代的舞台技术,根据爱森斯坦的说法,“这让他的演员技艺重现了似真似幻的高水平。”17Robert Robertson, Eisenstein on the Audiovisual: The Montage of Music, Image and Sound in Cinema, London: I.B. Tauris, 2011, pp.78.
在台湾海峡另一端,当时还在日本殖民时期,一群安德烈·布勒东和让·科克多的爱好者组织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群体,以法文风车“Le Moulin”为名。台湾导演黄亚历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日曜日式散步者》讲述了30年代的风车诗社。关于为什么是超现实主义,黄如此回答:“我觉得超现实主义要被引号起来,因为超现实主义不等于风车诗社 ,[…]且超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脉络中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 18Sun Songrong and Jiang Boxin, Accelerating Towards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terview Huang Yali on the Dream, Arts and Politics of Le Moulin, Taipei, August, 2016, pp. 91
将所谓的“原始主义”或极其现代的“超现实主义”概念打上引号,这正是去殖民化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1930年代的先锋派,从东京到台北,从墨西哥城到莫斯科,再到巴黎,上海,他们诞生于忧患,传播迅速,扣人心弦,他们的全球性,世界主义的特质,非常能够穿透历史,也反映了任何新生文化在形成时总是拾人牙慧的状态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实际上也是相互穿透)的过程堪称令人眼花缭乱,大量借鉴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事物,借鉴那些来自“未来的原始人”和“过去的超现实主义者”。
但是——这些影响或相互渗透却并不弭平差异(这是殖民主义所做的或至少是试图做到的),也绝非意味着现代性就是“欧洲遗产”(这是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捍卫者的说法),或者同质化的消费主义“地球村”(这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商学院课程中给未来经理人们提到的中文“智慧”之谈:在中文里,危机一词既代表危险,也代表机会)。
让我再一次引用何塞·拉巴萨(José Rabasa)的话:“正如同欧洲在将美洲大陆(的巧克力,可可豆 [……] 以及高尚野蛮人的说法,食人,荒野,新世界,亚美利加)融入自身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之后,欧洲仍旧是欧洲,‘同样的’,美洲大陆在将欧洲的生活形态融入自身之后,仍是一块美洲大陆。在此,挪用,征用和弃用的过程是一条双向街。” 19José Rabasa, Tell Me the Story of How I Conquered You: Elsewheres and Ethnosuicide in the Colonial Mesoamerican Wor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2011, pp 11.
当然,这并不是要保留边界,保留“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反,它们的独特身份只有在彼此的混乱纠缠来确立,与其说是双向通道,不如说是一条十字路。这些都在在证明古人的明智,他们说:痛则不通。
让我以另一种种族主义笑话作结。我要说的不是中文莫名其妙,如果这些人肯花点时间学学外语,他们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外语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来看看以讹传讹这个英文称为“中国式耳语”的传话游戏。这个名字当然还是源于“中文莫名其妙”这一殖民话语。不过这个在中文叫做“以讹传讹”的游戏本身正呈现了文化互动和翻译的过程。如果说,各种学术研究动辄借鉴1930年代以前各种非西方国家知识的行为可以算是一种“以讹传讹(英文作‘中式耳语’- Chinese Whisper)的话,那么我们正好可以趁此好好检视这则游戏的规则:嘴巴发声,传到耳朵,由一窍传到另一窍,这不正是《易经》中象征安定通达的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要是再换一个说法,这就正如阿莫多瓦30年多前的经典电影《崩溃边缘的女人》(1988)中的一帧名场面:女主人翁佩帕被两把手枪指着,她一一介绍着西班牙凉菜汤独家配方中的原材料,接着特别说道,“做好它的秘诀就是——搅拌均匀”。
原文为英文,由陈玺安中译。
向在荣是昆山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助理教授及艺术副主任。他写有专著《古怪之道:一种去殖民探究》(2018)。他是柏林世界文化宫“小世界主义周末”的主策展人,并于2020年编辑出版了同名画册。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艺术、文学、哲学、宗教、性/别等诸多领域,并围绕着这些领域在西班牙文、英文、中文、法文、纳瓦特语世界中的去殖民轨迹而展开。他作为超图像小组(董冰峰、向在荣、滕宇宁)的成员,曾共同策划2021年广州影像三年展。目前他正专注第二部专著的写作,以及对“跨二元论”及“山寨”这两个概念在全球南方特别是拉美及中国框架下的研究。
陈玺安,策展人。《黑齿》杂志的共同编辑。